在书法艺术的星河中,总有一些身影看似“不合时宜”——他们不慕虚名,不逐时风,甘愿以“愚人”自居,却用一生的执拗守住了笔墨的根脉,所谓“愚人”,非真愚,而是一种大智若愚的境界:于临摹时“笨拙”地重复千遍,于创作中“固执”地坚守本心,于传承里“愚钝”地不计得失,这种“愚”,恰是书法艺术最珍贵的底色,是穿越时光的精神锚点。

“愚”在基础:临池学书,守拙以立根
书法之道,始于“用笔”,而成于“结字”,而“用笔”与“结字”的根基,正是日复一日的临摹,真正的“愚人”书法家,从不轻视这“笨功夫”,王羲之七岁学书,十二岁临习父亲王旷的书法,后遍学卫夫人、钟繇、张芝等前贤,临池学书,池水尽墨,这种“愚拙”的重复,让他在笔法中融会贯通,终成“书圣”,颜真卿少时家贫,无钱购买纸笔,用笔醮黄土水在墙上练字,后来师从张旭,又从“屋漏痕”中悟得笔意,其楷书雄浑开阔,正是源于对基础“愚而不舍”的坚守。
当代书法家启功先生,晚年常以“老顽童”自居,练字时却一丝不苟,他曾说:“书法没有捷径,就是一笔一画地写。”为了让结字更精准,他甚至自制“九宫格”练字本,反复对比碑帖中的结构,这种“愚”到极致的认真,让他的书法既有古法底蕴,又具个人风骨,反观当下一些书者,急于求成,跳过临摹直接创作,笔下或流于轻浮,或陷于狂怪,恰是少了这份“守拙”的“愚”。
“愚”在心境:淡泊名利,静心以养气
书法是心画,心境决定笔墨,所谓“愚人”,往往甘于寂寞,不为名利所动,怀素和尚练字“无纸可书”,乃种芭蕉万余株,以蕉叶为纸,反复挥洒,蕉叶写尽,竟将漆盘磨穿,其自述“忽然绝叫三五声,满壁纵横千万字”,看似“癫狂”,实则是将全部心力倾注于笔墨,忘却世俗纷扰,这种“愚”,是对外界的屏蔽,是对内心的专注。
弘一法师李叔同,早年才华横溢,书画、音乐、戏剧无所不通,却在盛年出家,以“弘一”为名,专研书法,他的书法早年秀逸,晚年却归于“朴拙”,线条如绵里裹铁,字字透露着“悲欣交集”的人生况味,他曾说:“应使文艺以人传,不可人以文艺传。”这种将名利置之度外的“愚”,让他的书法超越了技法层面,成为心性的流露,反观当下,一些书者热衷于参展、获奖、炒作,笔下满是“讨巧”的技法,却少了书法应有的“静气”,恰是心境浮躁所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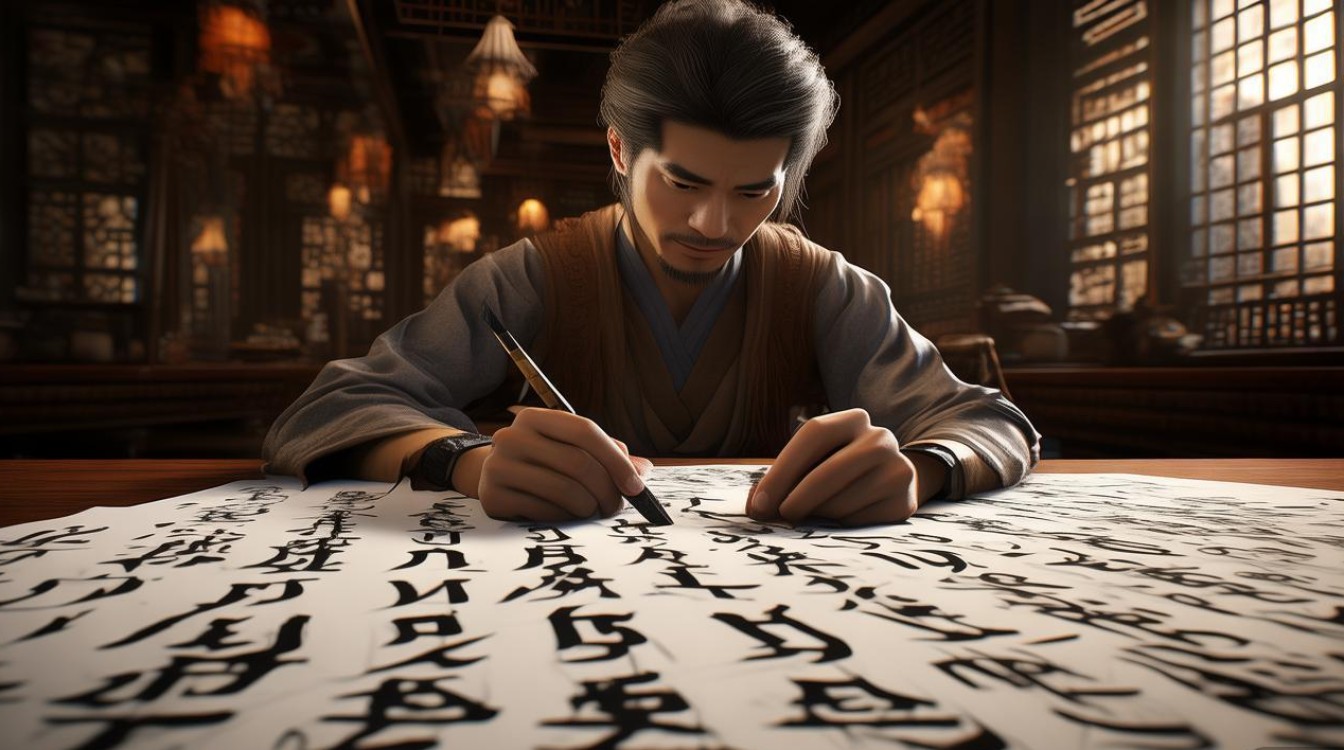
“愚”在创新:看似“愚”破,实则智生
书法艺术贵在创新,但创新绝非凭空臆造,真正的“愚人”书法家,往往在“守正”的基础上,以“愚”的执着打破常规,形成个人风格,金农是“扬州八怪”之首,他的书法早年学传统,五十岁后却自创“漆书”——以方笔扁体为主,如“横截两寸,直勒累尺”,看似“笨拙”,却打破了当时帖学流美之风,开碑学先河,他曾说:“耻向书家作奴婢,华山片石是吾师。”这种“耻为奴婢”的“愚”,正是对传统“食古不化”的反叛,对“自我”的坚守。
徐渭的书法更是“狂怪”中见“愚拙”,他的草书笔势奔放,如“飞鸟惊蛇,怒猊抉石”,看似杂乱无章,实则情感喷薄,将书法的抒情性发挥到极致,他曾自言“高书不入俗眼,入俗眼者非高书”,这种“不媚俗”的“愚”,恰是创新的前提——不被外界眼光束缚,只为表达内心,创新从不是对传统的否定,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后的“破茧成蝶”,而“愚人”的“固执”,正是这“破茧”的力量。
“愚”在传承:甘为“薪火”,不计得失
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传承,而传承往往需要“愚人”般的坚守,敦煌藏经洞中,无数无名写经生用毕生心血抄写佛经,他们的书法或许没有名家风范,却让魏晋笔法得以保存;明清之际,一些民间书者默默耕耘,将书法技艺传授给乡野孩童,让文脉在底层延续,他们不求青史留名,只愿“薪火相传”,这种“愚”,是书法艺术的“大爱”。
当代书法家魏启后先生,一生致力于书法传承,他不仅精研晋唐宋元经典,还热衷于培养年轻书者,他曾说:“书法不是个人的事,是文化的事。”晚年他将自己收藏的古籍、字画捐赠给博物馆,开设公益书法班,这种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的“愚”,让书法艺术在新时代焕发生机,反观当下,一些书者将书法视为“私有财产”,秘技不授,作品不传,恰是少了这份“愚”的胸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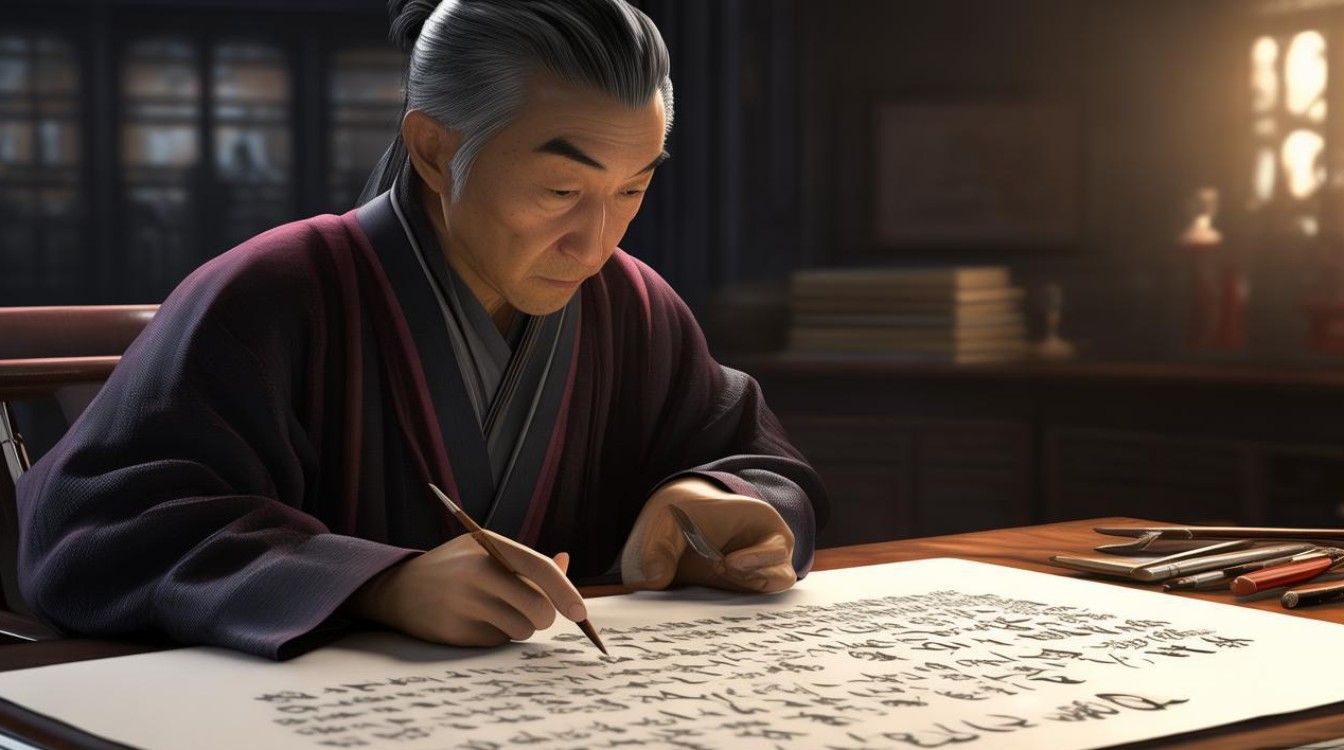
书法“愚人”的“愚”与“智”辩证观
| 维度 | “愚”的表现 | “智”的体现 | 典型代表 |
|---|---|---|---|
| 学习态度 | 甘于重复千遍,专注基础笔法 | 在重复中悟道,融会贯通传统 | 王羲之“池水尽墨”、颜真卿“墙练黄土水” |
| 创作心境 | 不慕虚名,屏蔽外界干扰 | 以心运笔,书法成为心性的自然流露 | 怀素“种蕉练字”、弘一法师“朴拙归真” |
| 创新路径 | 拒绝跟风,不媚世俗眼光 | 在传统基础上打破常规,形成个人风格 | 金农“漆书”、徐渭“狂草” |
| 传承精神 | 默默耕耘,不计个人得失 | 以文脉延续为己任,甘为“薪火” | 敦煌写经生、魏启后“公益教学” |
书法家的“愚人”精神,是一种“大智若愚”的生命哲学:它不是对世界的无知,而是对艺术的敬畏;不是对进步的拒绝,而是对本质的坚守;不是对传承的漠视,而是对文脉的担当,在这个追求“速成”“流量”的时代,这种“愚”愈发珍贵——它提醒我们:真正的艺术,从来不是“聪明”的投机,而是“愚”的坚守;不是外在的炫技,而是内心的沉淀,愿书法家们都能以“愚人”自居,在笔墨中守住初心,让书法艺术在“愚”的坚守中,生生不息。
FAQs
问:为什么书法家自称“愚人”是一种境界?
答:书法家自称“愚人”,并非真的愚蠢,而是一种“大智若愚”的自省,这种“愚”体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对传统的敬畏,甘于“笨拙”地临摹基础,不急于求成;二是对名利的超脱,屏蔽外界干扰,专注于内心表达;三是对创新的执着,在守正的基础上打破常规,不媚世俗,正如金农“耻向书家作奴婢”,徐渭“高书不入俗眼”,这种“愚”是对艺术本质的坚守,是超越技法的智慧,故称“境界”。
问:当代书法家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践行“愚人”精神?
答:当代书法家践行“愚人”精神,需做到“三不”:一不“追风”,面对纷繁的书法流派和时风,保持独立思考,不盲目跟风;二不“取巧”,抵制“速成”“流量”的诱惑,沉下心研究传统,夯实笔法基础;三不“藏私”,以传承文脉为己任,通过教学、展览等方式分享技艺,让书法艺术走进大众,需像弘一法师那样“应使文艺以人传”,将心性修养融入书法,让笔墨成为精神的载体,而非外在的炫耀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