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广州当代美术的生态图谱中,志刚是一位以深耕本土、锐意创新而备受瞩目的画家,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,他的艺术生命始终与这座城市的肌理紧密相连——从西关大屋的青砖石路到珠江新城的摩天轮廓,从木棉烈烈的红到榕荫深深的老,他用画笔为广州书写了一部视觉化的“城市志”,也在岭南画坛开辟出融合传统笔墨与当代精神的独特路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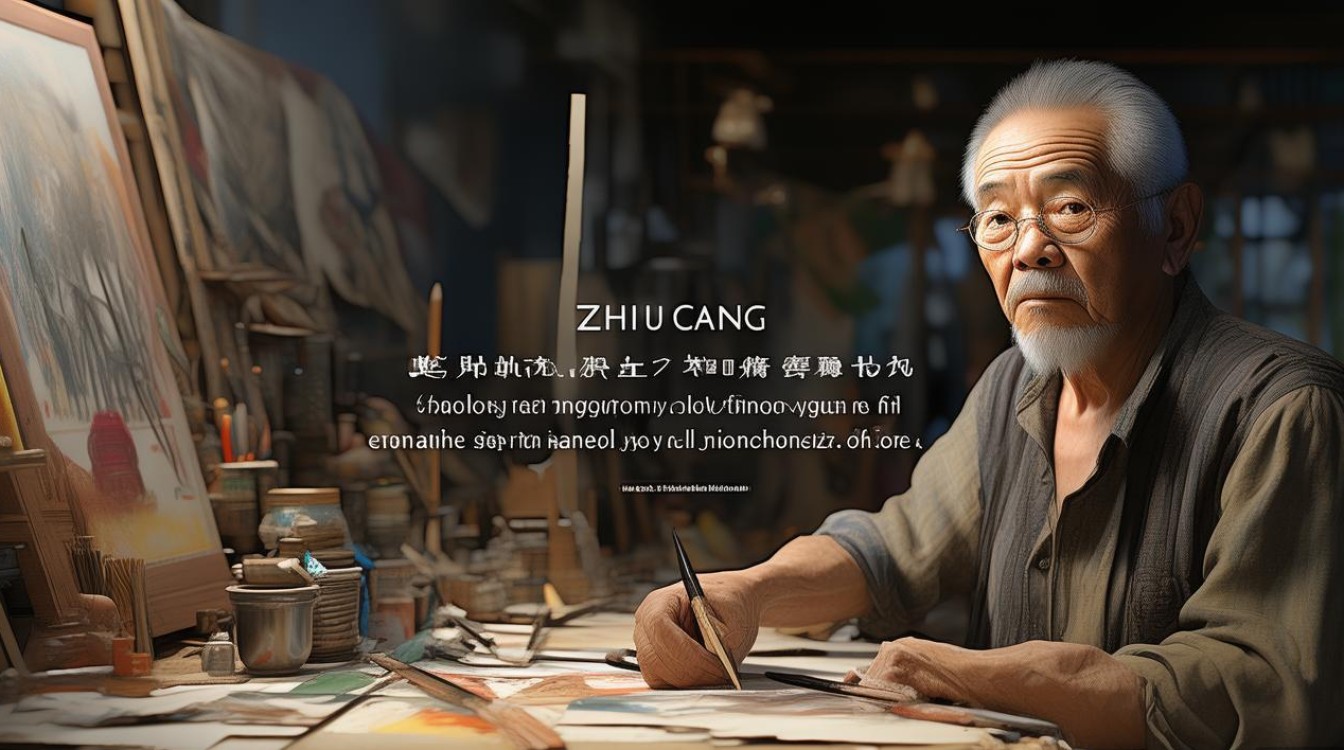
志刚的艺术启蒙始于少年时对西关骑楼与珠江景致的痴迷,上世纪80年代,他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,系统研习传统山水、花鸟与人物画,在校期间,他既深谙“岭南画派”高剑父、陈树人等前辈“折衷中西、融汇古今”的艺术主张,又深受杨之光等人物画大家“笔墨当随时代”理念的影响,毕业后,他没有选择留校或进入专业画院,而是背着画板穿梭于广州的大街小巷——在上下九的骑楼下观察市井百态,在沙岛的渡口记录晨昏光影,在陈家祠的砖雕前临摹传统纹样,这种“在场式”的观察与体验,为他后来的创作埋下了“以本土为根”的种子。
志刚的艺术风格以“写意都市”为核心,历经三十余年探索,逐渐形成“笔墨凝练、色彩明快、意境苍茫”的独特面貌,他的创作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,每个阶段的风格演变都清晰可见其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与突破:
早期(1990-2000年):以“市井风情”为主题,侧重对广州日常生活场景的写实描绘,受岭南画派“写生”传统影响,他常用小写意技法捕捉骑楼下卖肠粉的老伯、珠江边划龙舟的汉子、荔枝湾荡舟的姑娘,线条质朴灵动,色彩淡雅清新,充满生活气息,这一时期的作品如《西关晨早》《荔湾小景》等,虽技法尚显稚嫩,但已展现出他对本土文化的敏感与热爱。
中期(2001-2015年):进入“意象都市”探索期,开始突破具象写实的束缚,融入表现主义手法,随着广州城市化进程加速,志刚敏锐捕捉到城市变迁中的矛盾与张力——老城区的消逝与新城的崛起,传统记忆与现代文明的碰撞,他尝试用大写意笔触概括建筑轮廓,以浓烈的撞色(如赭石与群青、朱砂与墨色)对比营造视觉冲击,作品中的“人”逐渐符号化,而“城”成为主角,代表作《拆迁日记》《珠江新城组画》等,以粗犷的墨块与飞白的线条,勾勒出推土机与骑楼并存、钢筋森林与榕树根须交织的复杂图景,引发观者对城市发展的深层思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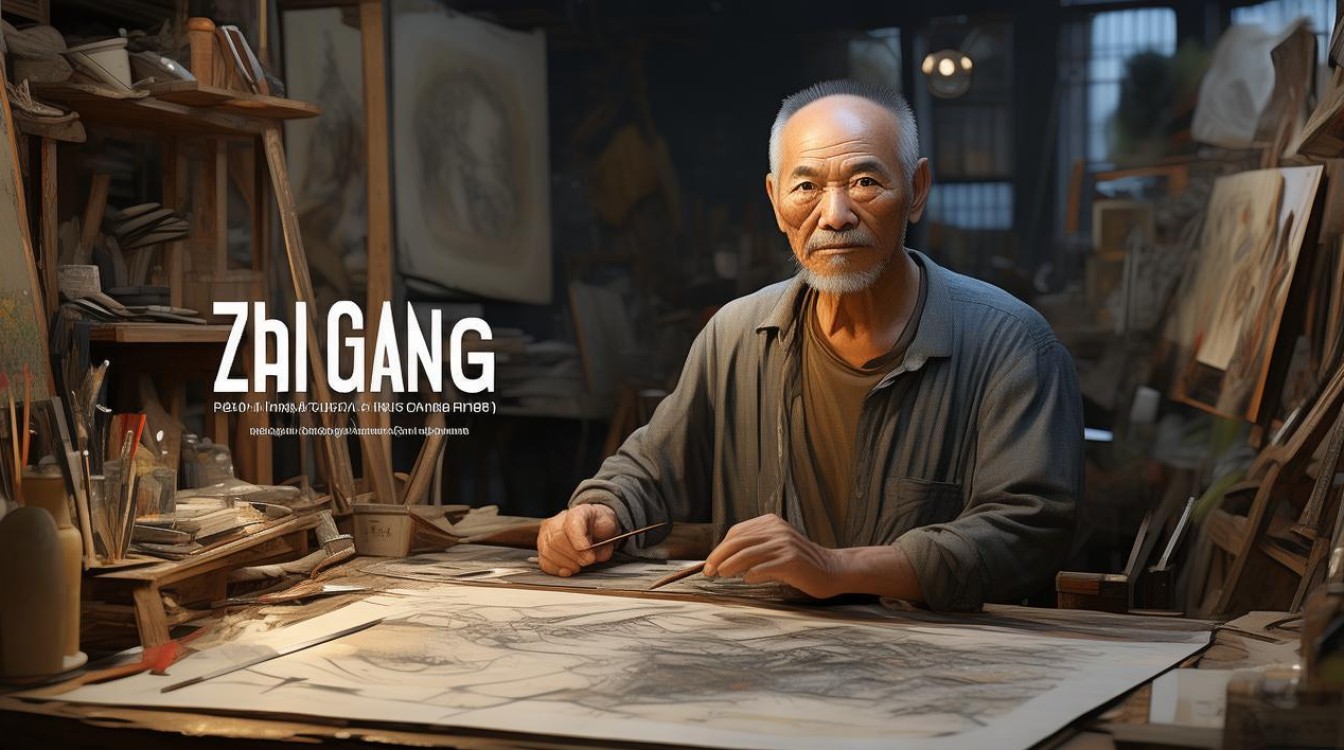
晚期(2016年至今):迈向“抽象都市”的升华期,传统笔墨与当代艺术语言达到高度融合,他不再满足于对城市形态的描摹,而是致力于捕捉广州的“精神气”——木棉的孤傲、榕树的包容、珠江的奔流、岭南人敢为人先的韧劲,这一时期的作品多采用大尺幅宣纸,以泼墨、泼彩为基础,辅以勾、皴、点、染,形成“墨中有色、色中有墨”的朦胧意境,如《木棉魂》系列,以朱砂泼洒出木棉的烈烈,再用浓焦墨勾勒遒劲枝干,背景用淡墨晕染出城市天际线,传统花鸟画的“形神兼备”与现代抽象画的“情感宣泄”在此完美结合;《榕荫千年》则用层层叠叠的墨色堆积出榕树的繁茂,细笔点缀的气根如城市的脉络,既是对自然生命的礼赞,也是对广州千年文脉的隐喻。
以下为志刚艺术风格演变简表:
| 时期 | 核心主题 | 技法特点 | 色彩倾向 | 代表作品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早期(1990-2000) | 市井风情 | 小写意,线条灵动,构图写实 | 淡雅清新,以水墨为主 | 《西关晨早》《荔湾小景》 |
| 中期(2001-2015) | 意象都市 | 大写意,融入表现主义,强调对比 | 浓烈撞色,墨色交融 | 《拆迁日记》《珠江新城组画》 |
| 晚期(2016至今) | 抽象都市(精神气韵) | 泼墨泼彩,抽象与具象结合,笔墨凝练 | 墨色交融,以朱砂、赭石为主 | 《木棉魂》《榕荫千年》 |
在题材选择上,志刚始终围绕“广州”这一核心母题,却从未陷入重复,他笔下的广州,既是地理空间,更是文化符号——木棉是英雄城的图腾,榕树是岭南人的精神家园,珠江是承载城市记忆的动脉,他曾说:“广州的美,不在精致的园林,而在市井的烟火;不在规整的街道,而在那些看似杂乱却充满生命力的角落。”这种对“不完美之美”的偏爱,让他的作品跳出了传统山水画的“隐逸”与“雅致”,呈现出一种鲜活的、接地气的当代性。
除了绘画创作,志刚还致力于岭南文化的推广与传承,他多次在广州、北京、香港及海外举办个人画展,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广东美术馆、广州艺术博物院等专业机构收藏;他走进社区、学校开设“画说广州”公益讲座,用通俗的语言向市民普及岭南画与城市文化的关系;他还参与“老广州街区保护”等社会议题,以艺术家的视角为城市记忆发声,正如艺术评论家所言:“志刚的画,不仅是艺术品,更是广州的‘活态档案’,他用画笔告诉我们:一座城市的魅力,在于它如何在变迁中守护自己的根。”

相关问答FAQs
Q1:志刚的绘画如何体现岭南文化的“当代性”?
A1:志刚对岭南文化当代性的体现,首先在于题材的突破——他跳出了传统岭南画“花鸟鱼虫”“山水胜景”的局限,将目光聚焦于快速城市化中的广州都市景观,如拆迁中的老街区、拔地而起的新地标、市井与摩登并存的生活场景,这些都是岭南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新表达,在技法上,他既保留岭南画派“写生”与“色彩”的传统,又融入西方表现主义的情感张力与抽象艺术的构成意识,形成“笔墨为骨、色彩为肉、时代为魂”的独特语言,珠江新城组画》中,他用传统山水画的“皴法”表现玻璃幕墙的光影,用鲜艳的色块对比呈现新旧城区的碰撞,让岭南文化不再是“博物馆里的标本”,而是流动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存在。
Q2:志刚的艺术创作对年轻画家有哪些启示?
A2:志刚的创作对年轻画家的启示主要有三:其一,“立足本土”的重要性——他证明,艺术不必追逐宏大叙事或潮流符号,深耕自己脚下的土地,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发现美,就能创作出有温度、有辨识度的作品,其二,“传统与创新”的平衡——他没有割裂与传统的关系,而是在笔墨、气韵上继承岭南画派的精髓,同时大胆吸收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法,这种“守正创新”的路径,为年轻画家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范本,其三,“艺术的社会责任”——志刚不仅用画笔记录城市,更通过展览、讲座、社会参与等方式,让艺术介入公共生活,启发年轻思考:艺术家的价值不仅在于创作,更在于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回应时代、服务社会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