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飞峰,当代中国画坛备受瞩目的艺术家,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厚的笔墨功底,在山水画与花鸟画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,他1965年出生于山东济南,自幼浸润于齐鲁文化的深厚底蕴中,少年时便展现出对绘画的敏锐感知力,后考入山东艺术学院,师从著名山水画家张志民先生,系统学习传统中国画理论与技法,后又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深造,受教于龙瑞等名家,艺术视野不断开阔,逐渐形成了兼具传统精神与当代意识的面貌。

公飞峰的艺术创作始终秉持“师古人、师造化、师心源”的理念,在传统方面,他深入研究宋元时期的山水画经典,对范宽的雄浑、倪瓒的萧疏、黄公望的浑厚均有独到体悟;花鸟画则取法徐渭的奔放、八大山人的简逸,兼收吴昌硕的朴拙,将文人画的笔墨意趣与写生精神相结合,在写生中,他足迹遍布黄山、泰山、桂林及江南水乡,对自然山川的观察细致入微,强调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,将自然物象升华为艺术意象,其作品既保留了传统中国画的笔墨韵味,又注入了当代人的生活体验与审美追求,展现出“澄怀观道”的精神境界与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考。
公飞峰的绘画语言独具特色,在山水画中,他擅长以“高远”“深远”相结合的构图,营造雄阔而灵动的空间感,用笔上刚柔并济,皴法多变,或披麻皴、斧劈皴,或解索皴、米点皴,根据山石质感灵活运用;墨色上注重层次,浓淡干湿相济,常以积墨法表现山体的厚重,破墨法表现云雾的流动,形成“墨分五色”的丰富效果,花鸟画则工写结合,工笔部分精细入微,如翎羽的花纹、花瓣的脉络,一笔不苟;写意部分则酣畅淋漓,枝干的苍劲、叶子的舒展皆以简练笔墨概括,形神兼备,色彩运用上,他既重视传统水墨的纯粹,也适度引入淡彩或重彩,如山水画中赭石、花青的晕染,花鸟画中朱砂、胭脂的点染,使画面在雅致中透出生机。
以下是公飞峰部分代表作品的概览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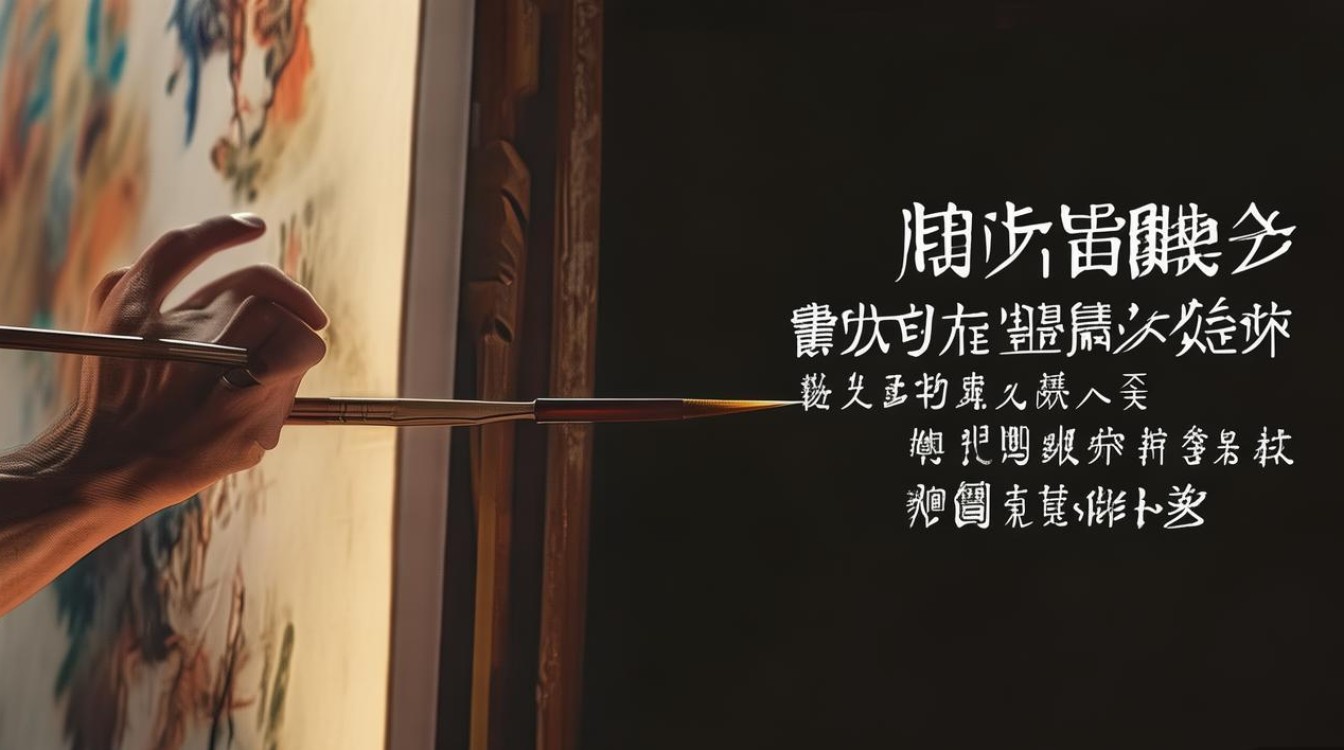
| 作品名称 | 创作年份 | 尺寸 | 材质 | 艺术特色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《岱宗秋色》 | 2018 | 240×120cm | 纸本水墨 | 以泰山为题材,取“旭日东升”之景,运用斧劈皴表现山石坚硬,积墨法渲染秋日山林的苍茫,云雾留白处见空灵。 |
| 《荷塘清趣》 | 2020 | 96×60cm | 绢本设色 | 工写结合,荷瓣以没骨法晕染,粉白透亮;荷叶以焦墨勾勒,筋脉分明;水草以写意笔法挥洒,体现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高洁。 |
| 《溪山行旅图新境》 | 2021 | 180×97cm | 纸本水墨淡设色 | 融合范宽《溪山行旅图》的雄浑与当代构成意识,近景树木精细刻画,中景溪流蜿蜒,远景烟缈朦胧,行旅人物虽小却点睛。 |
| 《春山听泉》 | 2023 | 200×100cm | 绢本重彩 | 以青绿为基调,借鉴唐人金碧山水的辉煌,又融入水墨的写意,泉声隐于笔端,设色浓而不艳,展现春日山林的生机与静谧。 |
公飞峰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创作上,还表现在对传统艺术的传承与推广中,他多次参与国内外重要展览,如“全国中国画展”“当代中国山水画名家邀请展”等,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上海美术馆等多家机构收藏,他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,担任多所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,通过授课、写生采风等形式,培养了一批青年画家,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,其艺术理念与作品被收录于《中国当代名家画集》《当代山水画研究》等权威出版物,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画转型的重要案例。
公飞峰的艺术之路,是传统与现代碰撞、融合的缩影,他以笔墨为媒介,将自然之美、人文之思熔铸于一纸,既坚守了中国画的文脉精神,又回应了时代的审美需求,在当代画坛独树一帜,其作品不仅给人以视觉的享受,更引发观者对生命、自然与文化的深层思考。
相关问答FAQs

Q1:公飞峰的绘画风格是如何逐步形成的?
A1:公飞峰的艺术风格形成经历了一个“传统奠基—写生体悟—融会创新”的过程,早期在山东艺术学院学习时,他系统临摹宋元山水画经典,打下了坚实的笔墨基础;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深造期间,受龙瑞等名家影响,深入研究传统画论,强调“以书入画”;其后通过大量写生,遍游名山大川,将传统笔墨与自然物象结合,逐渐形成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创作理念;近年来,他进一步融入当代审美意识,在构图、色彩上进行探索,最终形成了雄浑中见灵动、传统中有创新的个人面貌,其风格既体现齐鲁文化的厚重,又兼具江南文人画的雅逸。
Q2:公飞峰在创作中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关系?
A2:公飞峰认为传统是创新的根基,创新是传统的延续,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统一,在传统方面,他坚持“笔墨当随时代”,深入研究传统画理画法,如宋人的丘壑经营、元人的笔墨意趣,将其作为创作的“源头活水”;在创新方面,他注重从当代生活中汲取灵感,通过写生捕捉自然的新鲜感,在构图上打破传统范式,如采用构成意识增强画面张力,在色彩上适度引入新材料或调和技法,如青绿与水墨的结合,使作品更具时代气息,但他始终强调“守正创新”,创新不等于背离传统,而是在理解传统精神基础上的拓展,确保作品既有中国画的本体语言,又能反映当代人的精神世界,实现“传统为体,创新为用”的艺术追求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