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历史上,“奸臣”与“书法”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标签,常常出现在同一人物身上,他们或以权谋私、祸国殃民,却在笔墨间展现出非凡的艺术造诣,形成了“恶书”与“艺才”的复杂交织,这种现象背后,既有古代文人“立身”与“立艺”的错位,也折射出历史评价中“人品”与“艺品”的争议。

从历史背景看,古代书法是文人立身之本,无论是科举取士、公文书写,还是文人雅集,书法都是必备技能,即便如秦桧、蔡京等后世公认的奸臣,早年也接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,将笔墨视为进身的阶梯,当他们在权力场中走向堕落,书法便成了矛盾体——一面是艺术上的精益求精,一面是政治上的臭名昭著,这种矛盾,使得他们的书法作品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“被贬抑—被遗忘—被重新审视”的曲折过程。
以秦桧为例,作为南宋初年的宰相,他主和误国、构陷岳飞,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;但书法史上,他却是有名的“宋体字”鼻祖,据《宋史》记载,秦桧“善大字,益以取媚”,其书法造诣深得宋徽宗真传,笔法圆润流畅,结构方正严谨,甚至影响了后世的印刷字体,明代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评价他“书体姿媚,专尚黄(庭坚)米(芾)父子”,足见其艺术水准,因“奸臣”身份,他的书法作品在后世几乎被销毁殆尽,“秦体”之名也被刻意回避,直到近现代才有人客观评价其书法价值。
蔡京的情况更为典型,作为“六贼”之首,他结党营私、搜刮民脂,导致北宋末年政治腐败;但书法史上,他本与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并称“宋四家”(后因品行被蔡襄取代),其书法“沉着痛快”,笔力雄健,代表作《节夫帖》《草书千字文》至今仍被视为经典,苏轼曾赞其“当与二十人并驱争先”,米芾也承认其书“功力深矣”,随着政治失势,蔡京的书法被斥为“奸书”,作品大量散佚,甚至有人刻意将其书法题跋改为他人之名,以“去恶存善”。
明代严嵩亦是如此,他专权二十余年,党同伐异、贪污受贿,被《明史》列入《奸臣传》;但书法造诣颇高,擅长行草,笔法婉丽遒媚,嘉靖年间的许多碑刻、匾额都出自其手,如北京“孔庙”“天坛”的匾额传说即为他所书,因其政治污点,这些匾额在后世多次被毁或替换,书法成就也被刻意掩盖。

这种“因人废书”的现象,本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字如其人”观念的体现,古人认为“书为心画”,书法品性直接反映人品,奸臣的“心术不正”自然会被投射到笔墨间,使其艺术成就被贬低,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,学界逐渐意识到:艺术成就与政治品行不应简单画等号,剥离政治因素,单从书法技法看,这些奸臣的作品确实有其独特价值——秦桧的“方正”为印刷体定型,蔡京的“笔力”展现了宋代尚意书风的巅峰,严嵩的“婉丽”反映了明代台阁体的审美特征。
以下是部分“奸臣”书法代表人物简表:
| 人物 | 朝代 | 书法成就 | 历史评价 |
|---|---|---|---|
| 秦桧 | 南宋 | 创“宋体字”,笔法圆润,影响印刷体 | “奸臣”,书法被刻意回避,近现代渐受关注 |
| 蔡京 | 北宋 | “宋四家”之一(后除名),笔力雄健,代表作《节夫帖》 | “六贼之首”,书法称“奸书”,作品大量散佚 |
| 严嵩 | 明代 | 擅长行草,笔法婉丽,曾书孔庙、天坛匾额 | 《明史》奸臣,书法作品被多次销毁替换 |
| 赵高 | 秦代 | 书写《爰历篇》(小篆范本) | “指鹿为马”奸臣,书法成就被政治掩盖 |
客观而言,奸臣的书法艺术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复杂遗产,它既警示我们权力对人性的腐蚀,也提醒我们艺术评价的独立性——即便是最可鄙的人,也可能在某一领域展现才华;即便是最厌恶的人,其作品也可能包含美学价值,正如启功所言:“书恶何必论人品,堪恨常称方正学。”对待这类书法,我们不必因其作者品行而全盘否定,也不应因艺术成就而为其历史污点开脱,而是应在“知人论世”的基础上,理性看待艺术与政治的复杂纠葛。
FAQs
问: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奸臣书法水平很高?
答:古代书法是文人立身之本,奸臣多出身士族,需通过书法博取信任、进阶仕途;长期书法训练培养了其笔墨功底,使其在艺术上达到较高水准;部分奸臣(如秦桧)掌权后,甚至利用政治资源推广书法,进一步提升了艺术影响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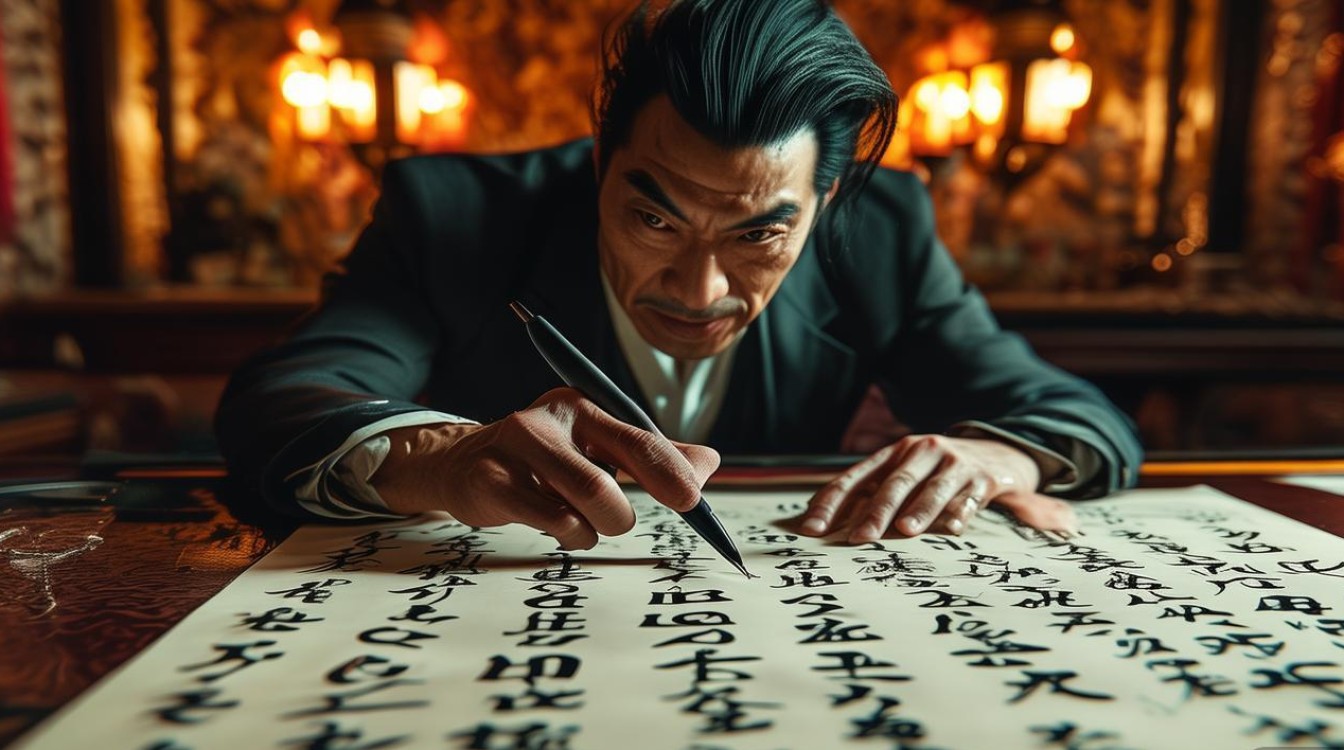
问:如何评价奸臣的书法成就?
答:应区分“艺术价值”与“历史评价”:技法层面,肯定其笔法、结构、气韵等艺术成就,如蔡京的笔力、秦桧的字形;历史层面,需结合其政治行为,明确其奸臣身份,避免因艺术成就美化其人,艺术成就可研究,但历史污点不可遗忘,需辩证看待“艺”与“人”的关系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