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,“春”从来不仅是自然节律的标识,更是生命哲思的载体、情感寄托的符号,当书画家以笔墨为媒,将“春”凝于纸绢,便超越了物候的描摹,成为一场跨越千年的艺术对话——他们笔下的“春”,是工笔重彩里的繁花似锦,是水墨淋漓的烟雨迷蒙,是疏朗淡雅的枯木逢春,更是文人心中“生生不息”的精神图腾。

书画家笔下的“春”,首先是一套丰富的意象符号系统,花鸟画中,牡丹以“国色天香”代言盛春,花瓣层叠如锦,叶脉舒展似碧,宋徽宗赵佶《芙蓉锦鸡图》里的牡丹,与锦鸡相映,尽显宫廷画院的富丽春光;桃花则以其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烂漫,成为文人春意的私语,明代沈周《写生册》中的桃花,以淡墨勾勒,胭脂点染,带三分野趣,七分雅致;而燕子,作为“春的使者”,其剪刀尾掠过水面,衔泥筑巢的身影,几乎成为所有书画家都无法绕过的春之符号——宋代佚名《百花图卷》中,双燕穿梭于花丛,动态轻盈,仿佛能听到呢喃声穿纸而出,山水画里,“春”是“春山淡冶如笑”的温润,北宋郭熙《早春图》以卷云皴绘山石,淡墨渲染烟岚,树木吐出新芽,整幅画如被春晨的薄雾浸润,山石似在微笑;元代倪瓒《渔庄秋霁图》虽以秋为题,但其“逸笔草草”的笔法,若移至春景,便是对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空灵春意的最好诠释,人物画中,“春”是“踏青”“游春”的生活场景,南宋李嵩《观潮图》虽以潮景为主,但远景中踏青的人群,三五成群,衣袂翩跹,将春日的闲适与生机融入市井烟火。
不同朝代的书画家,对“春”的诠释也烙着时代的印记,宋代院体画追求“格物致知”,其笔下的“春”是精致入微的客观再现——如《百花图卷》中,从牡丹的娇艳到梨花的素净,从蝴蝶的斑纹到蜜蜂的绒毛,皆以精细的笔法刻画,春色如工笔镜头般纤毫毕现,体现着宋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观察的入微,元代文人画兴起,“春”转向主观心境的抒发,倪瓒笔下的春景,多为疏林坡岸、浅水遥岑,笔墨简淡,意境清冷,所谓“逸笔草草,不求形似”,实则是将春意融入“胸中逸气”,春在他的画中不再是繁盛,而是一种“素以为绚”的平淡天真,明代书画个性解放,“春”呈现出多元面貌——沈周的写意花鸟,春意质朴醇厚,带有文人的烟火气;徐渭的大写意泼墨,以狂放的笔法绘葡萄、石榴,春在他的笔下是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的激情与悲怆,绚烂中带着生命的张力;清代石涛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,其《春江图》以破墨、泼墨结合,春江浩渺,烟波浩荡,山石以“截断法”构图,打破传统程式,春景在他眼中是“无法而法”的流动与变化,近现代以来,齐白石的“春”是泥土芬芳的田园春趣,《春耕图》中耕牛奋蹄,农人弯腰,笔墨简练却充满生命力,他用“衰年变法”的写意精神,让春意回归最本真的民间生活;徐悲鸿的《春山驴背图》,将西方素描的明暗与中国画的笔墨结合,春山巍峨,驴背行人,刚健的线条中透着春日的蓬勃朝气。
书画技法与“春”的呈现密不可分,工笔重彩的“春”,依赖“三矾九染”的耐心:宋代《碧桃图》中,桃花的花瓣以白粉打底,胭脂分染,层层叠加,近看如能触到花瓣的柔嫩;叶子的正面以花青染,背面以汁绿染,叶脉以细笔勾勒,春光的明媚与花朵的娇嫩在细腻的技法中呼之欲出,写意水墨的“春”,则讲究“墨分五色”的韵味:明代徐渭的《墨葡萄图》,以泼墨葡萄藤表现春日的生机,葡萄藤以浓墨、淡墨交替挥洒,干湿浓淡间,藤蔓的盘曲、新芽的萌动尽在笔墨之外,所谓“似与不似之间”,正是春意的朦胧与灵动,构图上,全景式的大场景(如北宋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中的春山绵延)展现春的宏大气象,折枝式的小品(如清代恽寿平《瓯香馆写生册》中的折枝桃花)则聚焦春的细节之美,以小见大,于方寸间见春意,色彩上,青绿山水的“春”是“金碧辉煌”的盛唐气象,王希孟以石青、石绿层层敷染,春山如宝石般璀璨;水墨写意的“春”是“墨海中立定精神”的文人情怀,八大山人以水墨绘枯荷、残鸭,春意藏于萧疏之中,更显孤高与坚韧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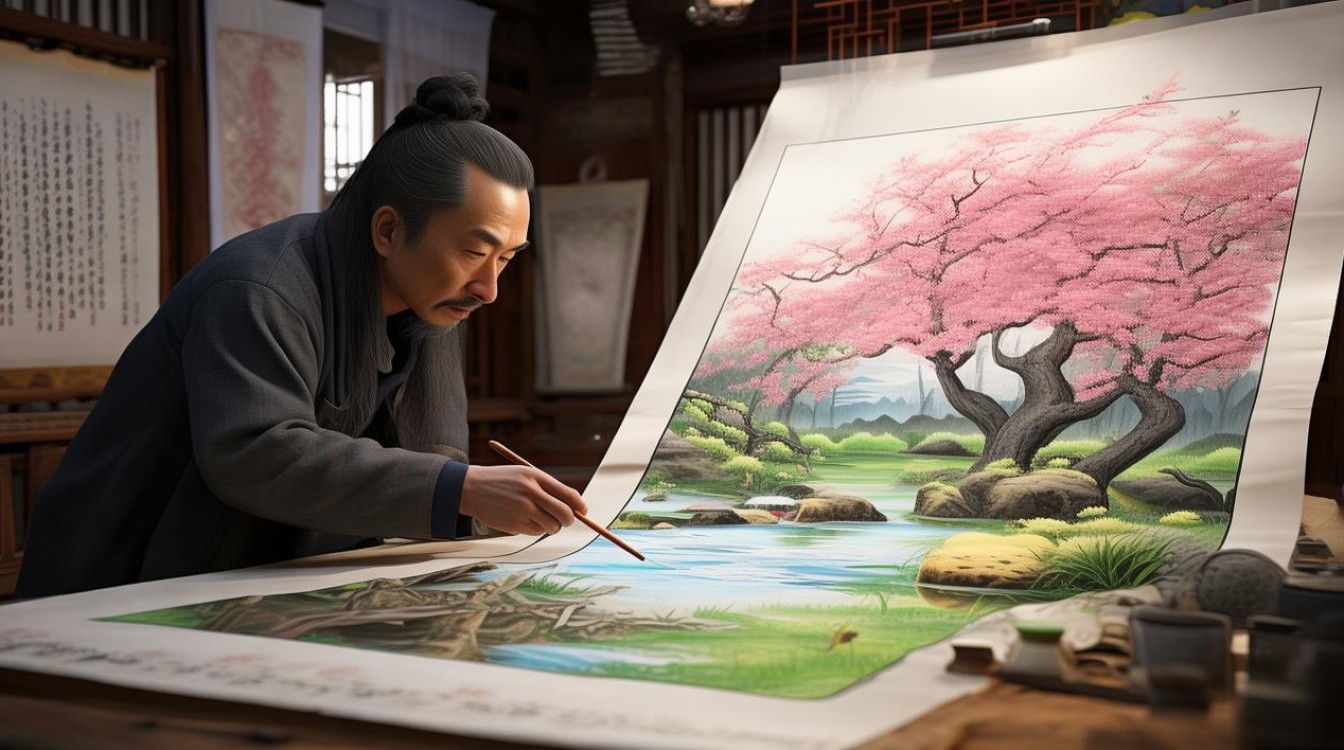
更深层次看,书画家的“春”是文化精神的凝结,儒家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让“春”成为宇宙生命力的象征——《周易》言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书画家笔下的春之萌动、春之繁盛,正是对“生生不息”的宇宙观的视觉诠释,如宋代马远《山径春行图》中,老者拄杖行于山径,前方柳枝新绿,春水初生,人与自然在春意中和谐共生,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哲学,则让“春”呈现出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自然之美——元代吴镇《渔父图》中的春江,一叶扁舟,渔父垂钓,远山含黛,春水无波,春意不事张扬,却在平淡中见大道,文人“寄情山水”的情怀,更让“春”成为情感的载体——王维“春来遍是桃花水,不辨仙源何处寻”,以春景寄托对理想世界的向往;苏轼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”,以春景表达对生活的敏锐感知与旷达胸襟,民间画中的“春”,则带着吉祥的期盼——年画《连年有余》以莲花、鲤鱼与春景结合,“莲”谐“连”,“鱼”谐“余”,春日里的丰收与富足,是百姓最朴素的春之向往。
从宫廷画院的富丽春光,到文人画斋的淡雅春意;从工笔的精细描摹,到写意的酣畅淋漓;从自然的客观再现,到心灵的主观抒发——书画家笔下的“春”,是一部流动的艺术史,更是一面映照中华文化精神的心灵之镜,当我们在千年后的今天,凝视这些画中的春色,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生命力:那是牡丹的绚烂,是燕子的呢喃,是春山的微笑,更是中华文化对“生”的永恒礼赞。
相关问答FAQs
问题1:书画家表现“春”时,为何常选用燕子、桃花等意象?
解答:燕子、桃花等意象之所以成为“春”的经典符号,源于其文化内涵与自然特性的双重契合,燕子是候鸟,春来秋归,其“归来”的动作直接对应季节更替,且燕子身形轻盈、动作敏捷,常穿梭于花间、屋檐,能生动传递春日的灵动与生机;在传统文化中,燕子还象征“吉祥”“和睦”,如“燕燕于飞,差池其羽”,常被赋予美好的情感寄托,桃花则是春日最具代表性的花卉之一,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的诗词意象,使其成为“青春”“美好”的象征,其花期短、绽放急的特性,也暗合春景“绚烂易逝”的哲思,二者共同构建了观众对“春”的直观认知——燕子的“动”与桃花的“静”结合,既有自然的生机,又有文化的温度,因此成为书画家表现“春”时的高频意象。

问题2:现代书画家在创作“春”主题时,与传统有哪些不同?
解答:现代书画家的“春”主题创作,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,意象选择更多元:传统“春”主题多围绕牡丹、桃花、燕子等经典符号,现代书画家则融入都市元素(如高楼旁的樱花、公园里的早梅)、生态符号(如春日的候鸟回归、城市绿化),甚至抽象符号(如用色块、线条表现春光的流动),使“春”的内涵从自然田园扩展到现代生活场景,情感表达更个性化:传统“春”多寄寓文人雅士的闲适、哲思或吉祥期盼,现代书画家则更关注个体对春的现代体验——如疫情后对“春之希望”的强调、对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思考,甚至通过“春”的意象表达对生命、时间的个体化感悟,情感更具私人性与当代性,技法融合更创新:传统以笔墨、色彩为主要工具,现代书画家则结合丙烯、综合材料、数字艺术等媒介,如用拼贴表现春花的层次,用数字喷绘增强春光的色彩张力,打破传统“笔墨中心论”,让“春”的表现形式更具实验性与视觉冲击力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