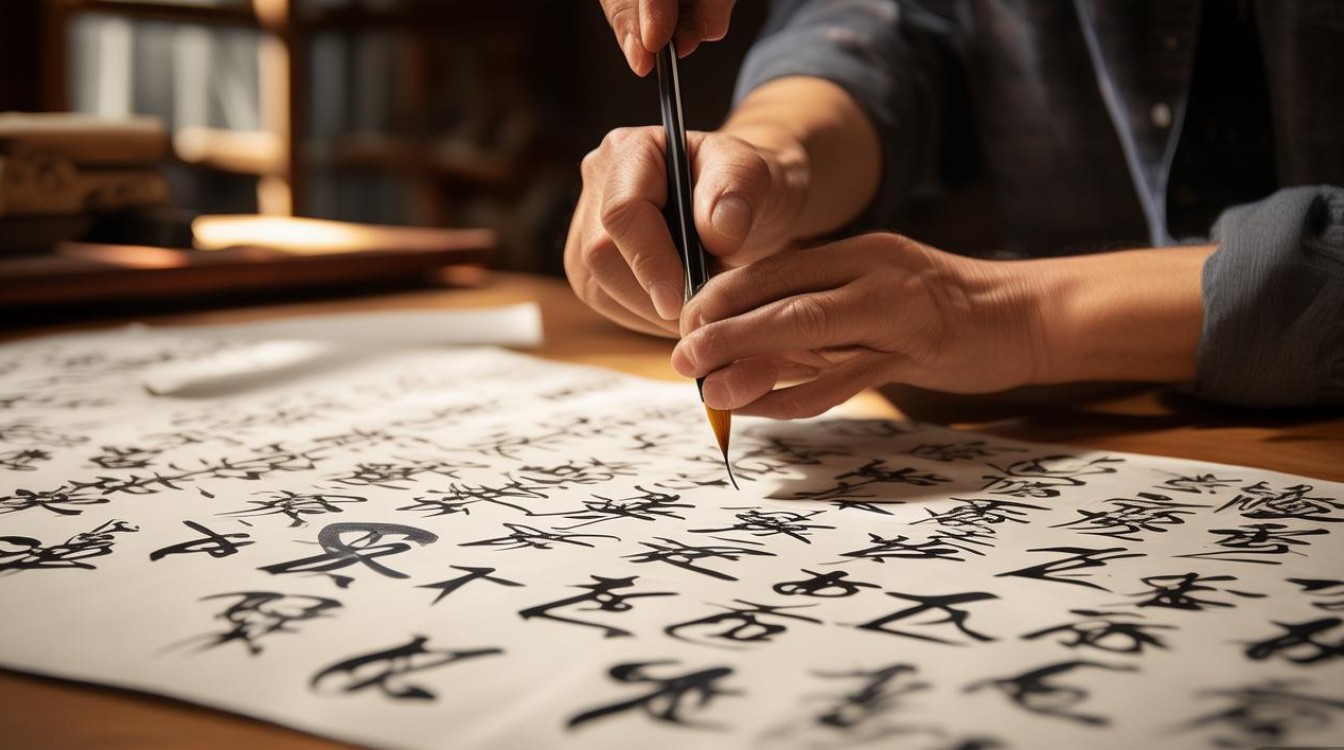书法中的“干作余”,是笔法、墨法与心法交织的独特审美体系,三者如同经纬,共同编织出书法艺术的肌理与灵魂。“干”并非枯槁干涩,而是以含墨较少的笔锋书写,形成枯、涩、苍、劲的笔触;“作”是创作者对笔墨的驾驭与经营,是技法与情感的融合过程;“余”则是笔尽而意无穷的余韵,是观者于笔墨之外生发的审美联想,三者相辅相成,共同指向书法“既雕既琢,复归于朴”的终极追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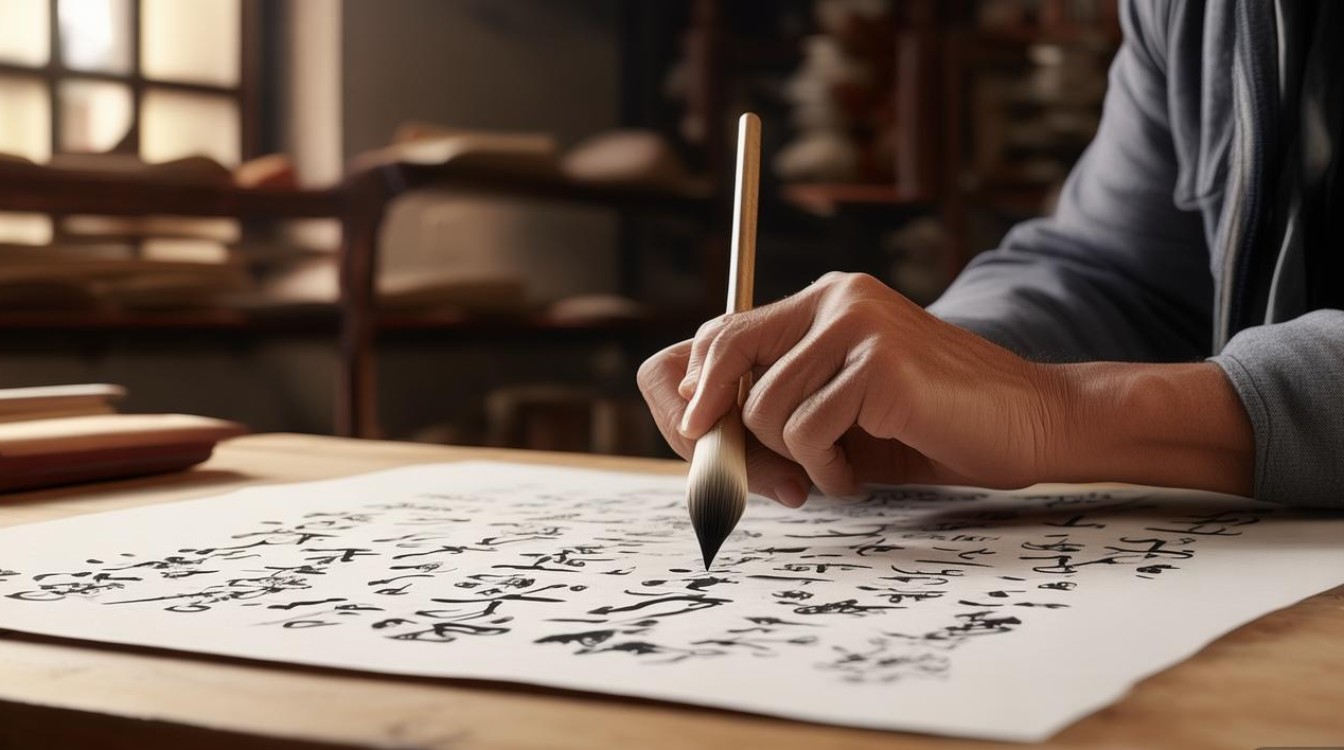
“干”的审美意蕴,源自书法对自然物象的抽象摹写,古人云“屋漏痕”,言雨水沿墙蜿蜒而下,干涩中见润泽,正是对干笔之美的生动诠释,从商周甲骨文的刻刀痕迹,到汉简的率意飞白,再到明清王铎、傅山的“涨墨飞白”,干笔始终是书法表现力的重要载体,其核心在于“燥润相生”:墨少则笔锋开叉,形成“飞白”的虚灵;纸墨相拒,则产生“涩笔”的阻力感,如锥画沙、屋漏痕,于艰涩中见遒劲,傅山曾言“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”,干笔的“拙”与“丑”,恰是对人工雕饰的反拨,彰显出自然天真的生命力,干笔的运用需“度”的把握,过则浮漂,不及则板滞,唯有“带燥方润,将浓遂枯”,方能于干涩中透出华润,如枯藤老树,愈显苍劲古拙。
“作”是“干作余”的核心实践,是创作者将内在情思外化为笔墨痕迹的过程,书法之“作”,非机械描摹,而是“意在笔先,作字先作人”的心手合一,创作时,创作者需调墨、执笔、运腕,三者协调统一:墨之浓淡干湿,需根据书体与章法调配;笔之提按顿挫,需顺应情感起伏;腕之虚实转换,需控制笔锋的使转,以行草为例,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“之”字,或干笔飞白如断金切玉,或湿笔圆转如行云流水,其“作”之妙,在于“若断还连,似有还无”的节奏变化,楷书之“作”则更重法度,欧阳询《九成宫》的干笔点画,如“高峰坠石”,于收笔处戛然而止,留下斩钉截铁的痕迹,正是“作”时对笔锋精准控制的结果。“作”的最高境界是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,既需对技法的千锤百炼,更需对自然与人生的深刻体悟,如此方能“心手双畅”,下笔如有神助。
“余”是“干作余”的审美延伸,是笔墨之外的精神回响,书法艺术之所以“无声之音,无形之相”,正在于其“余韵”悠长,干笔的“断”,常引发“连”的联想,如怀素《自叙帖》的枯笔飞白,笔丝虽断,气脉不断,似惊蛇入草,余势不绝;干笔的“燥”,常生“润”的遐思,如八大山人的枯笔荷石,墨色焦渴,却于空白处生出水汽氤氲,满纸荒寒中透出孤傲之气。“余”的产生,依赖于“计白当黑”的章法布局,干笔形成的“虚白”,与实笔形成对比,给观者留下想象空间,正如笪重光《画筌》所言“虚实相生,无画处皆成妙境”,书法的“余”,正是这种“无画处”的精神意蕴,它让笔墨超越形迹,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,承载着创作者的人格理想与时代精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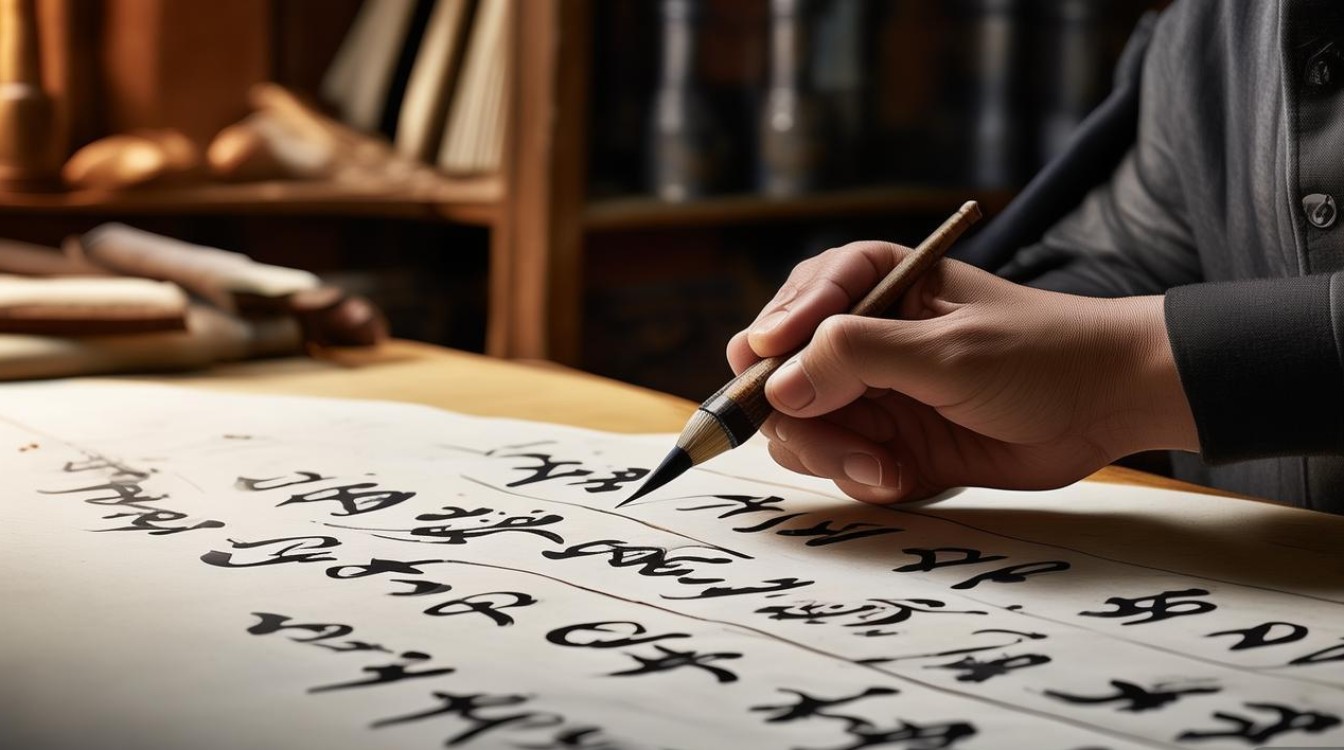
| 干笔类型 | 特点 | 艺术效果 | 代表书家/作品 |
|---|---|---|---|
| 枯飞白 | 笔丝开叉,墨色极淡,似有似无 | 空灵飘逸,如烟似雾,增强画面节奏感 | 王羲之《兰亭序》、怀素《自叙帖》 |
| 渴笔 | 笔锋含墨适中,运笔速度较快,笔毛略开 | 苍劲古拙,如老藤盘曲,体现金石味 | 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、傅山《草书轴》 |
| 焦笔 | 墨近枯竭,笔纸摩擦阻力大,笔锋枯散 | 老辣生涩,如万岁枯藤,展现生命张力 | 八大山人《河上花图卷》、徐渭《草书诗卷》 |
FAQs
-
问:使用干笔时如何避免“燥气”,让作品显得苍劲而不浮漂?
答:避免“燥气”需把握“三宜三忌”:宜“墨中加水”调节浓淡,忌墨过渴;宜“以指运腕”控制笔锋,忌僵直拖拽;宜“干湿交替”形成对比,忌通篇干枯,同时需注重笔力,如“锥画沙”般入纸,以力生润,方能“干而不燥,苍劲有神”。 -
问:初学者练习干笔技法,应从哪些方面入手?
答:初学者可分三步:先练“控墨”,通过调墨实验掌握墨与水的比例,感受从湿到干的变化;再练“运笔”,以中锋行笔为主,练习“提按”动作,体会笔锋与纸的摩擦力;最后临摹经典,如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的渴笔、王铎行草的飞白,在实践中领悟“干作余”的节奏与韵律,切忌盲目追求枯槁而忽视笔力与结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