舒勇,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极具辨识度的艺术家,他以水墨为根基,却不止步于传统笔墨的边界;他以社会为画布,将个体的思考与时代的脉搏熔铸于作品之中,而在他多元的艺术实践中,“木”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——它不仅是具体的创作媒介,更是承载其哲学思考、文化立场与人文关怀的符号,从湖南乡村的童年记忆到国际艺术舞台的先锋探索,“木”在舒勇的艺术世界里,既是物质的载体,也是精神的图腾,串联起他对自然、传统与社会的深层叩问。

舒勇与“木”:从乡土记忆到艺术自觉
1974年,舒勇出生于湖南湘西南的一个乡村,那里的山林田埂、木构老屋是他童年的底色,木材作为最朴素的材料,既是生活的工具(农具、家具),也是自然的馈赠(柴火、建材),这种与“木”的早期亲密接触,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对“物”的理解——木材并非冰冷的原料,而是有温度、有纹理、有生命的历史见证者,后来他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,系统学习传统水墨,又辗转北京、广州等地接触当代艺术,但“木”始终是他艺术探索中的“隐线”。
2000年前后,舒勇开始有意识地将“木”纳入创作,此时的他,正经历从水墨画家到当代艺术家的转型,他不再满足于宣纸上的笔墨游戏,而是试图寻找一种更具“在场感”的媒介,木材的天然肌理、沉重质感与可塑性,恰好契合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性表达——相较于平面的绘画,立体的木结构更能承载空间的叙事性,天然的木纹则自带时间的痕迹,他曾说:“木是沉默的,但它的每一道裂痕、每一圈年轮都在说话,我要做的,就是让这些‘沉默的声音’被听见。”这种对“木”的自觉选择,标志着舒勇艺术语言的逐渐成熟。
“木”的多重维度:媒介、符号与哲学
在舒勇的艺术中,“木”至少承载了三重意义:作为创作媒介的“木”,作为文化符号的“木”,作为哲学隐喻的“木”。
作为媒介的“木”,舒勇打破了传统木雕的工艺束缚,将木材的“不完美”转化为艺术语言,他偏爱使用老木料——废弃的房梁、老旧的家具、风化的树桩,这些木材历经岁月侵蚀,表面有虫蛀的孔洞、开裂的缝隙、烟熏的痕迹,在《尘》系列中,他将这些老木料切割、拼贴,保留其原始的粗糙质感,只在局部施以水墨或彩绘,让人工的笔触与自然的肌理形成对话,比如作品《老房子》,他用拆解的木梁搭建出一个微缩的民居结构,木梁上的斧凿痕迹与墨色的山水晕染交织,既是对乡村记忆的挽留,也是对城市化进程中“消逝的家园”的视觉化呈现。
作为符号的“木”,舒勇将木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五行”“山水”“文人精神”等意象结合,赋予其当代解读,在《山水入梦》系列中,他用整块木料雕刻出层叠的山峦,表面覆盖半透明的宣纸,宣纸上绘制的水墨山水若隐若现,木材的厚重与宣纸的轻盈形成对比,传统“山水”的永恒性被木材的“物质性”所解构——山不再是文人笔下理想化的精神寄托,而是具体的、可触摸的、承载着生态记忆的实体,这种“木与纸”的对话,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、自然与文化的碰撞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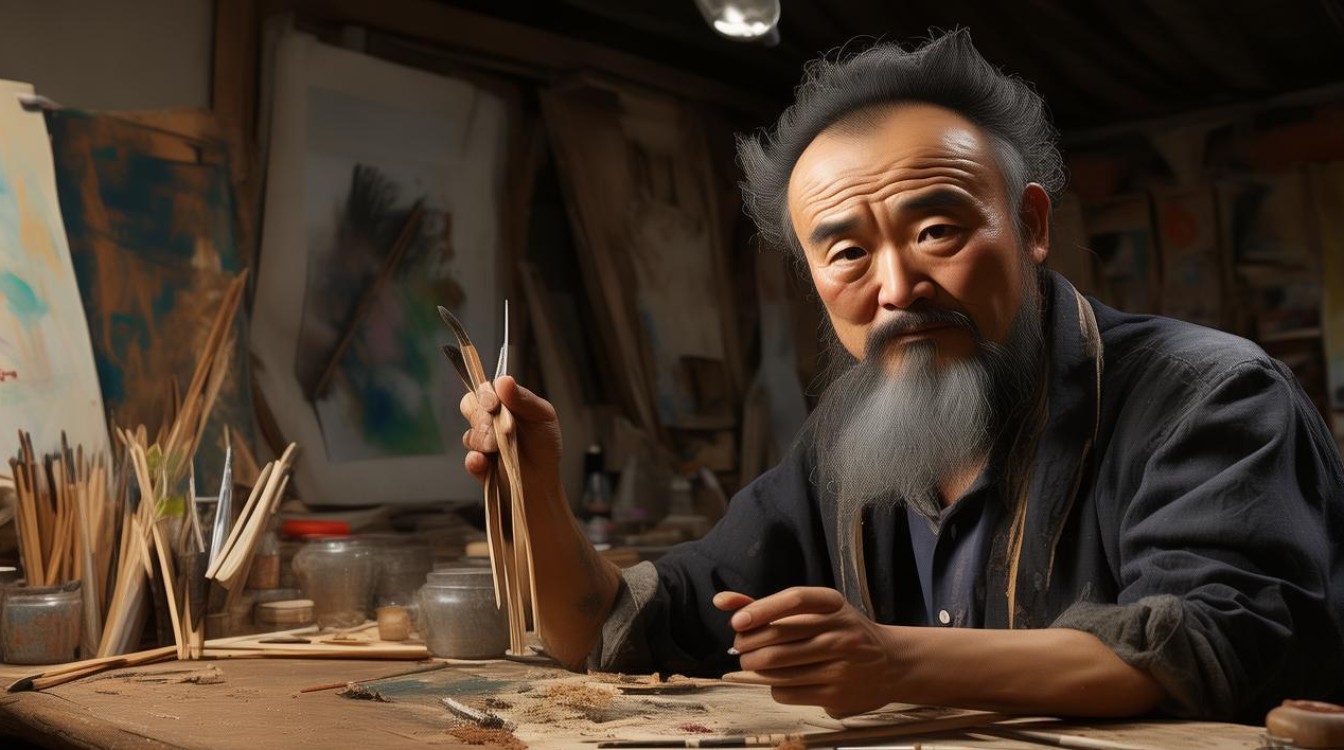
作为哲学隐喻的“木”,舒勇通过木材的“生长”与“腐朽”探讨生命的循环与时间的本质,他的《年轮》系列直接以树桩为原型,在保留原始年轮的基础上,用金粉、银粉填满每一圈纹理,或在其上镶嵌玻璃、金属等现代材料,年轮是树木的“记忆”,也是时间的“刻度”,当天然的年轮与人工的贵金属相遇,既是对生命力量的礼赞,也是对“时间在现代文明中被异化”的反思——我们是否正在用物质消费消解了时间的自然意义?
代表作品中的“木”叙事:用木材构建时代寓言
舒勇以“木”为核心的作品,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介入性,他用木材的“物性”讲述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,以下是他部分代表性“木”主题作品的梳理:
| 作品名称 | 创作年份 | 材料媒介 | 主题表达 | 艺术手法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《老房子》 | 2008 | 老房梁、木料、水墨 | 乡村记忆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园消逝 | 拼贴、保留木料原始纹理与斧凿痕 |
| 《山水入梦》 | 2012 | 整块木料、宣纸、水墨 | 传统山水文化的当代转化 | 木雕与水墨结合,半透明宣纸覆盖 |
| 《年轮》 | 2015 | 树桩、金粉、银粉、玻璃 | 时间、生命与文明的关系 | 年轮填嵌现代材料,对比自然与人工 |
| 《木与城》 | 2018 | 废弃木料、城市拆迁砖块 | 城市更新中物质与精神的冲突 | 木料与砖块搭建装置,呈现空间张力 |
| 《根脉》 | 2021 | 老树根、金属骨架、LED灯 | 文化传承与生命力的延续 | 树根与金属结合,LED灯模拟根系生长 |
这些作品并非孤立的艺术实验,而是构成了一个“木的叙事谱系”:从《老房子》对个体记忆的追溯,到《木与城》对城市问题的反思,再到《根脉》对文化生命力的探寻,“木”始终是连接个体与时代、传统与当下的桥梁,在《根脉》中,舒勇将百年老树根与金属骨架结合,树根的虬曲形态被金属的理性线条所“固定”,而嵌入其中的LED灯则发出幽幽蓝光,模拟根系在黑暗中生长的状态,这件作品既是对“根”的守护——传统文化如老树根,深植于历史土壤;也是对“生长”的期待——在当代语境下,文化需要新的“骨架”与“光源”才能延续。
“木”的价值:在当代艺术中锚定人文坐标
舒勇对“木”的运用,绝非简单的材料偏好,而是对当代艺术“去物质化”“观念化”倾向的反拨,在许多当代艺术家沉迷于数字媒介、虚拟空间时,他坚持用木材这种最“古老”、最“笨重”的材料,提醒人们关注“物”本身的存在——木材的温度、纹理、重量,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自然信息,这种“回归物质”的创作,让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“可触摸的真实感”,观众不仅能“看”,更能“感”——通过触摸木材的粗糙表面,感受时间的痕迹;通过理解木材的来源,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“木”也是舒勇连接传统与当代的纽带,他将水墨的写意精神、木雕的工艺传统融入当代艺术的语言体系,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刻,也不是对西方艺术的盲目追随,而是在“木”的媒介中,找到一种属于中国当代艺术的“文化自觉”,正如他所言:“木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的;它是传统的,但当代艺术赋予它新的生命。”这种以本土材料为根基的国际化表达,让舒勇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广泛认可,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“身份认同”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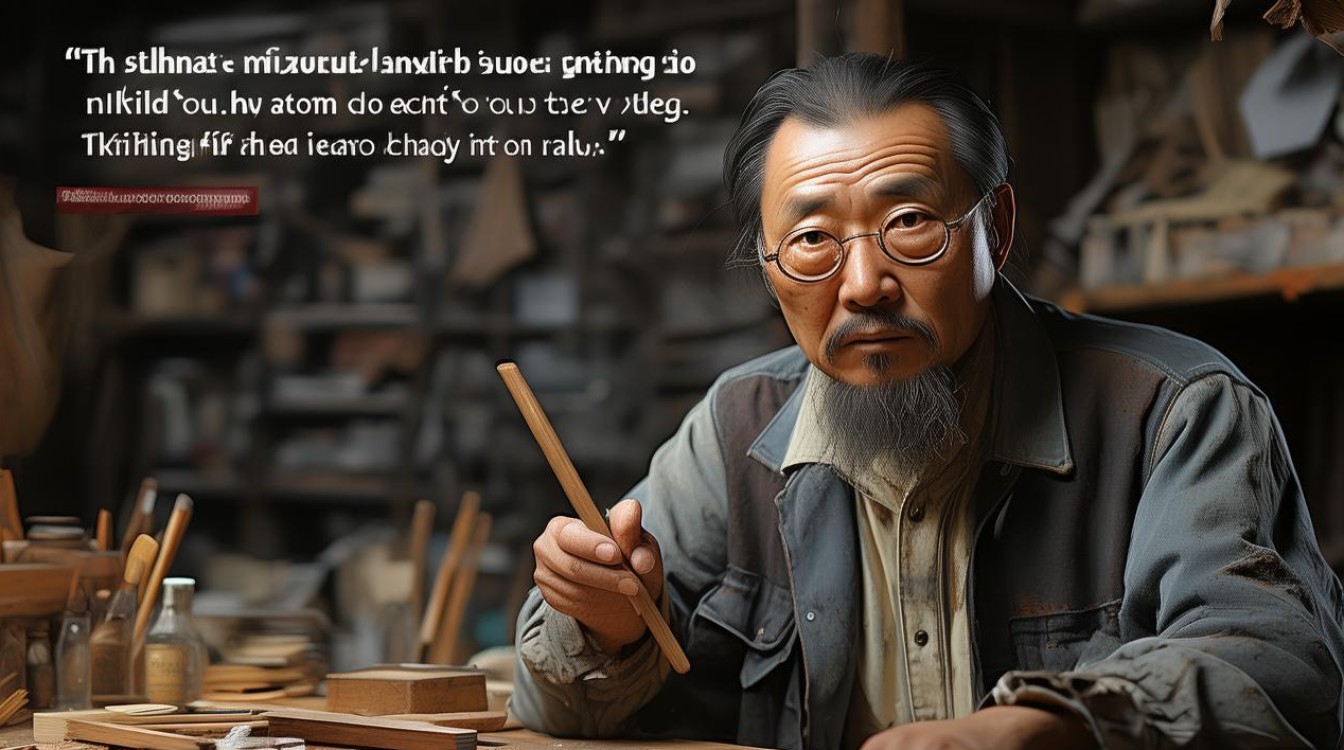
相关问答FAQs
Q1:舒勇在创作中为何偏爱“木”这一元素?它与其他创作材料(如水墨、金属)相比有何独特优势?
A:舒勇偏爱“木”,首先源于他与木材的早期生活记忆,木材的天然质感与温度承载着他的乡土情感与文化认同,木材作为媒介具有独特的优势:其一,它自带“时间性”——年轮、裂痕、虫蛀等痕迹是自然与历史的共同书写,能直观呈现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痕迹;其二,它具有“物质性”的重量感与触感,相较于平面的绘画或虚拟的数字媒介,木材构建的装置能让观众产生更直接的“身体在场”体验;其三,它具有“文化符号性”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“木”关联着“五行”“山水”“文人精神”等核心意象,便于将当代思考与文化基因结合,与水墨的“空灵”和金属的“冰冷”相比,木材的“温厚”与“矛盾”(既脆弱又坚固,既传统又现代)更能承载舒勇对社会现实的复杂态度。
Q2:舒勇的“木”系列作品如何体现对社会关怀的表达?能否举例说明?
A:舒勇的“木”系列作品始终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,他通过木材的“物性”转化,将社会问题转化为视觉寓言,木与城》(2018年),他用城市拆迁中废弃的木料与砖块搭建装置,木料的粗糙纹理与砖块的规整形态形成对比,既象征了城市更新中“自然”与“人工”、“记忆”与“发展”的冲突,也暗喻了个体在城市化浪潮中的渺小与坚韧,再如《尘》系列,他收集乡村老屋的木梁,保留其表面的烟熏痕迹与虫蛀孔洞,结合水墨绘制出模糊的人形或建筑轮廓,这些作品既是“消逝的乡村”的视觉档案,也是对“快速现代化中文化失根”的深刻反思,通过将“木”从日常材料提升为社会批判的载体,舒勇让观众在“看”艺术的同时,被迫思考“我们是谁”“我们从哪里来”“我们要到哪里去”的终极问题。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