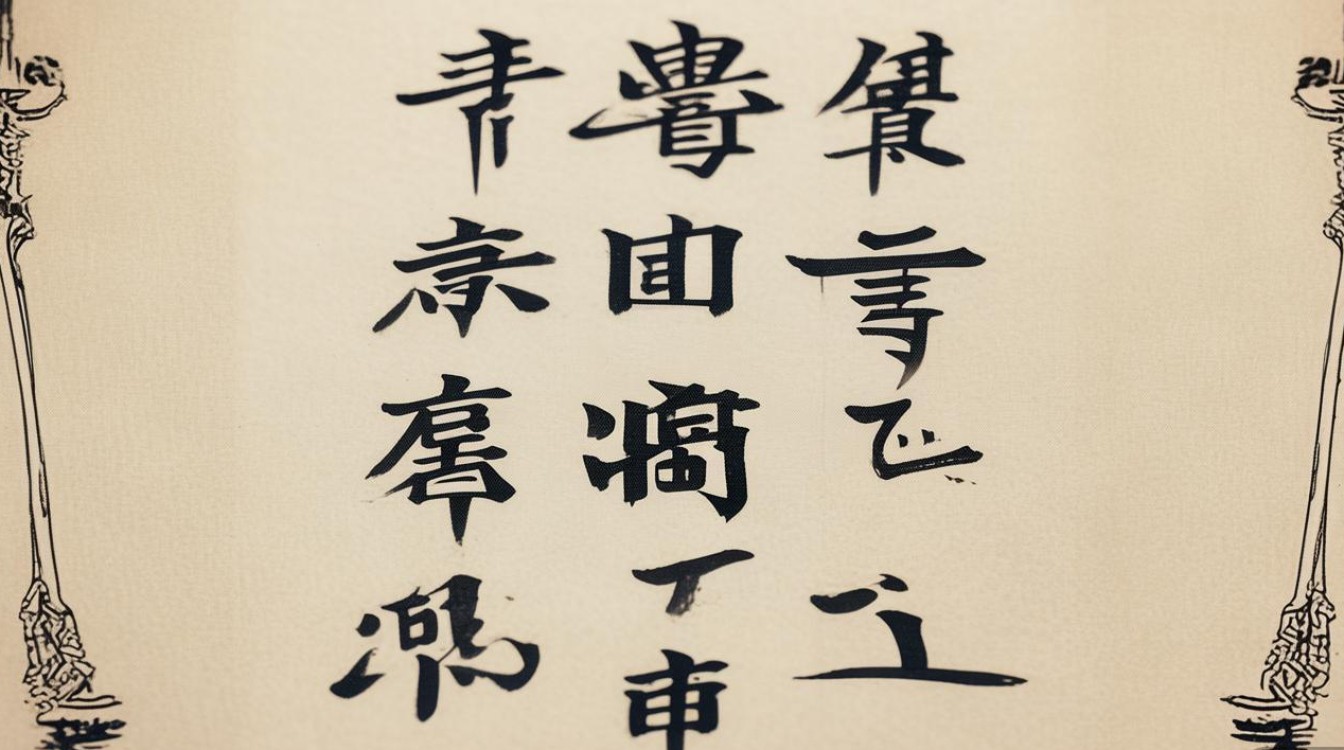书法中的“媚”,非艳俗之媚,而是线条流转间的灵动、结构疏密中的雅致、气韵贯通里的温润,是刚柔相济的审美境界,如“春山烟起,远岫云归”,既有形质之美,又含风神之韵,这种“媚”并非刻意雕琢,而是书家学养、性情与技法融合的自然流露,贯穿于书法史的发展脉络,成为评判作品气韵的重要维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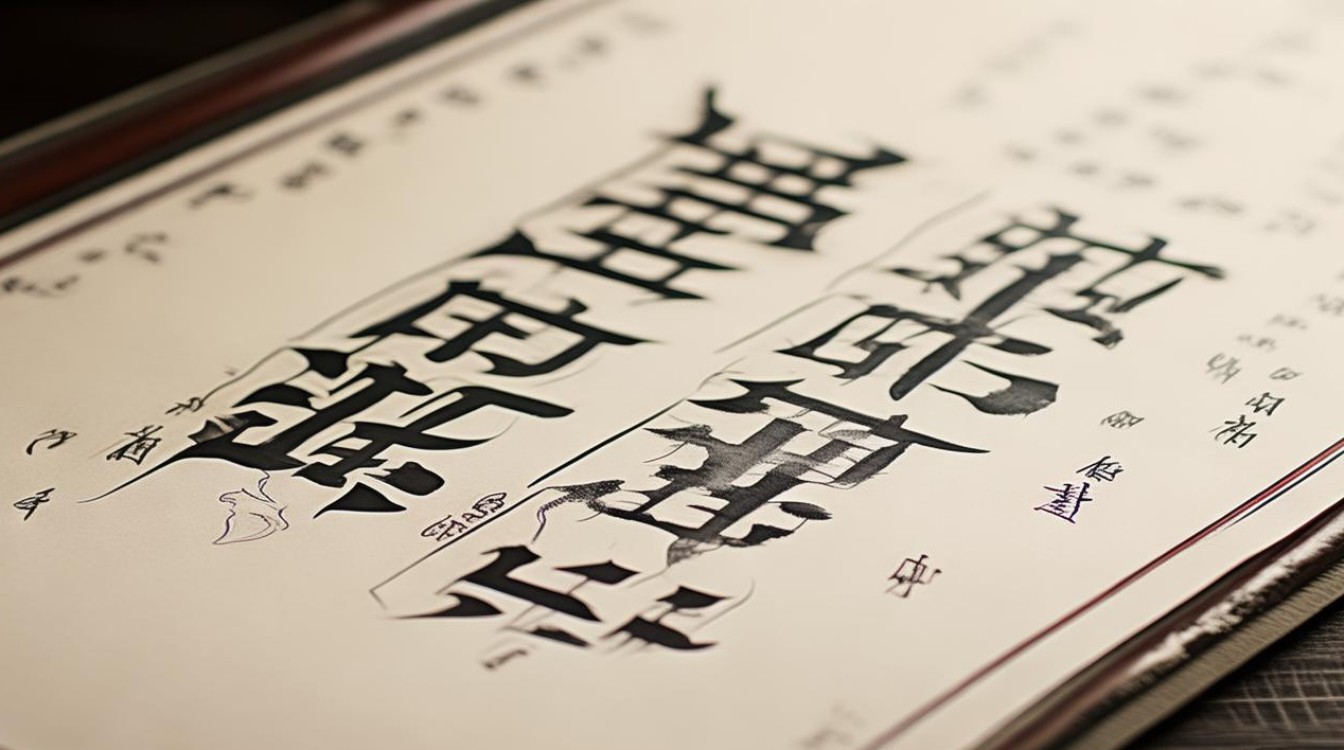
从历史演进看,“媚”之审美在晋唐已初具雏形,东晋王羲之《兰亭序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,其“媚趣”横生:线条如“美女婵娟,不胜罗绮”,起笔“一拓直下”含蓄藏锋,转折处“带燥方润,将浓遂枯”,既有力度又不失柔美;结构上“斜反正,密处不犯,疏处不离”,二十余个“之”字各具姿态,或欹或正,或疏或密,在变化中求统一,尽显“不激不厉,而风规自远”的“清媚”之境,唐代褚遂良《雁塔圣教序》化隶为楷,笔画细劲而富有弹性,如“铁线描”般柔中带刚,结体舒展开阔,如“舞鹤游天,流苏转月”,其“媚”在“瘦金体”前已开“秀媚”一派;薛稷善用“鹤头笔”,线条瘦劲而姿态婉转,转折处“如印印泥”,刚劲中见婀娜,成为唐代“媚”书的重要代表,宋代尚意,“媚”的审美转向率真自然,米芾“刷字”以“刷”求“媚”,笔势连绵如“风樯阵马,沉着痛快”,墨色浓淡相间,如“云烟变灭”,其“媚”在“意足我自足,放笔一戏空”的洒脱中,少了唐法的严谨,多了宋意的灵动,清代碑学兴起,“媚”的审美融入金石气,赵之谦以北碑为基,化用行书笔意,线条方圆兼备,如“绵里裹铁”,结体扁方而灵动,其“媚”在“碑帖融合”的新意中;吴昌硕以石鼓文笔意写行书,线条苍劲而带“金石气”,转折处“圆转自如”,老辣中见姿媚,为“媚”字书法注入雄浑之气。
技法层面,“媚”的表现需线条、结构、墨色的协同,线条是“媚”的筋骨,需“力道藏于内,姿态露于外”,如王羲之“屋漏痕”般的线条,看似自然天成,实则是“力透纸背”的内敛;转折处“提按顿挫”分明,如褚遂良“鹤头钩”般的弯钩,柔而不弱,弹性十足,结构是“媚”的骨架,需“违而不犯,和而不同”,如《兰亭序》“崇山峻岭”四字,“崇”字左窄右宽,“山”字上疏下密,“峻”字左欹右正,“岭”字左密右疏,在变化中形成视觉平衡,于险绝中求平正,尽显“媚”之姿态,墨色是“媚”的气韵,浓淡干湿相生,如米芾《蜀素帖》,“浓处如崩石,淡处如轻烟”,枯笔飞白如“枯藤缠树”,湿笔晕染如“春雨含烟”,在虚实间见“媚”之韵致。
需注意的是,“媚”需以“骨”为基,否则“媚”成“俗”,赵之谦“碑帖融合”之“媚”,有“金石气”为骨,故“媚”而不俗;馆阁体“乌、方、光”,结构板滞,线条僵化,徒有其“形”而无其“神”,是为“俗媚”,正如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言:“书尚清、厚、奇、古,短于清则无韵,厚则俗,奇则轻,古则板。”可见“媚”需与“清、厚、奇、古”相融,方能达“雅媚”之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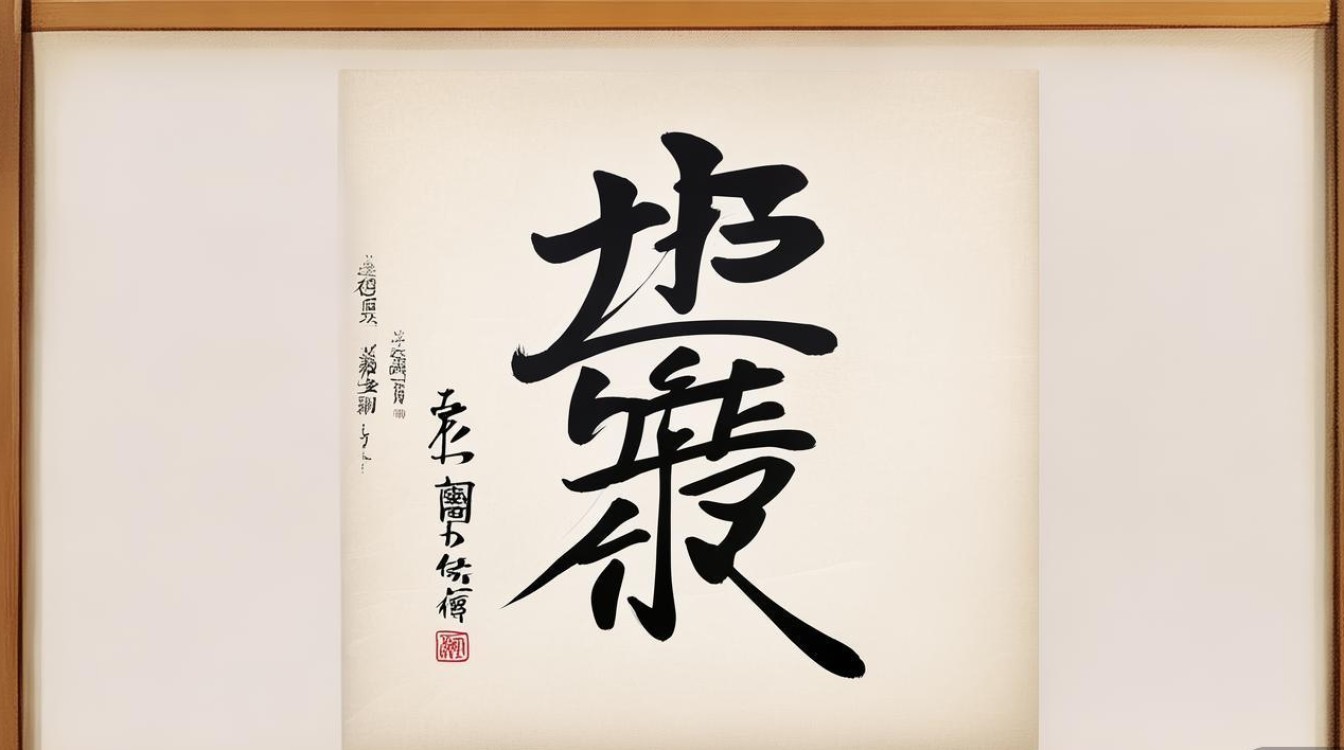
| 媚字书法代表书家及风格特征 | 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 | 书家 | 时代 | 风格特征 | 代表作品 | | 王羲之 | 东晋 | 线条流转如行云,结构欹侧呼应,气韵温润雅致 | 《兰亭序》《十七帖》 | | 褚遂良 | 唐 | 笔画细劲带弹性,结体舒展,清秀灵动 | 《雁塔圣教序》《阴符经》 | | 米芾 | 宋 | 笔势连绵率真,墨色浓淡相间,意态生动 | 《蜀素帖》《苕溪诗帖》 | | 赵之谦 | 清 | 碑帖融合,方圆兼备,扁方结体灵动 | 《楷书七言联》《行书四条屏》 |
FAQs
问题1:书法中的“媚”与“俗媚”有何本质区别?
解答:“媚”以“骨”为基,含学养、性情与技法,是“刚柔相济”的审美境界,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“媚”有“力道”与“气韵”支撑,线条柔美而不失刚劲,结构灵动而不失法度;“俗媚”则无“骨”,徒求形似,刻意追求姿媚,流于艳俗、板滞,如馆阁体的“乌、方、光”,缺乏个性与神采,仅为表面的“甜媚”。
问题2:初学者如何把握书法中“媚”的度?
解答:初学当先“立骨”,以楷书为基础,练好线条的力道与结构的端正,如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的“骨力”,避免线条软弱;再学“求媚”,临摹褚遂良、米芾等“媚”趣明显的作品,体会线条的流转与结构的灵动,如褚遂良的“细劲笔画”与“舒展结体”;需避免刻意追求“姿媚”,在扎实功底上自然流露,做到“媚而不俗,雅而不拙”,最终达到“无意于佳乃佳”的境界。